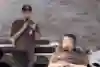音樂
四月三十日這天,節拍廣場創辦人DJ Chicano舉辦了一場為年輕人開講的細說台灣舞廳的黑歷史講堂,邀請台灣八零年代的DJ Stephen與DJ 小滕現身講述他們親身經歷的美好DJ時光。
本此台灣大舞講堂(#tbtDJ黑歷史)共分為二部份,一部份由Stephen前輩講述台灣舞廳早期的成形和發展,也就是現今人稱的夜店;另一部份則由小滕前輩以當時唱片採購且身兼DJ的經驗分享他的音樂心經,而台灣舞廳的大事紀光譜是如何演進?現在就來為大家完整回顧當日講堂之中,DJ Stephen前輩的詳述。
DJ Stephen:
大家好,今天來與大家講述分享台灣夜店的由來,以前叫夜總會、舞廳或迪斯可,名詞因年代而有所不同;那麼我今天將舉例解說的多以具代表性的舞廳為主,其他較小間或曇花一現的,在此就略過不提。以前的夜店娛樂場所,分為三種類型,第一種是夜總會型的迪斯可(disco),附屬於飯店之下的舞廳;第二種是pub,中美建交時期,駐臺的美軍顧問團所引進的酒吧文化,那時在中山北路的俱樂部,外國人會去那裡打撞球、聽聽歌,最早出現的時期還沒有DJ,只有點歌機,偶爾會有樂團表演。第三種類型則是Music House(音樂空間),它們本身是一間餐廳、咖啡廳或冰菓室,冰菓室就是以前大家吃剉冰的地方,由於大多是年輕人聚集地,通常會用錄音帶放送音樂,都是一些當時流行的西洋音樂。
夜總會迪斯可
回到第一種類型-夜總會型的迪斯可,也就是台灣的正宗迪斯可。為何說正宗呢?因為它的場域一定會有一座舞池、燈光,以及讓DJ放歌的DJ臺,通常也會有燈光師甚至舞者。第一家夜總會迪斯可在希爾頓飯店,也就是現在台北車站對面的凱薩大飯店。在1977年,當時希爾頓飯店的三樓開設了Tiffany夜總會,他們邀聘新加坡的DJ經紀公司讓專門放歌的人來狄斯可工作,於是指派了一名從新加坡培訓而成的台灣女DJ,這位女DJ也就是全台灣第一位DJ,她是毛珊。當時她從新加坡回台灣主導Tiffany夜總會的音樂策劃,也打開台灣DJ的第一道門。Tiffany夜總會的最低消費是一千二百元,相同於現在的台幣一萬多元,所以它在當時是高消費場所,也不普遍;出入消費的人多是達官顯要、名流紳士、影歌星和名模特兒,而且還會有人站在門口過濾客人,一般人不僅負擔不起,即使有消費能力也不見得能進去。
夜總會迪斯可在當年可說是娛樂場所的創舉,隔年,位在中山北路的中央飯店(現今的富都飯店)開了全台第二家狄斯可,影星唐威(藝人唐志中之父)想讓它普及化,於是他利用週六和週日的下午開設午場。前往午場消費的大多以學生為主,但一身制服和當時髮禁所留的五分頭就會被識破而進不去,因此會去舞廳的學生,通常會另有一個提袋,裡頭裝的是一套便服和假髮。午場是從一點半開始,學生下課後就去消費,跳舞跳到五點半。那時門票是一百五十元,可以換一杯紅茶或可樂,當時並沒有賣酒。再隔年(1979年)又開了二家迪斯可舞廳,分別是在喜來登飯店(當時為來來飯店)和華國飯店的頂樓,越來越多學生尤以大學生居多逐漸地接觸到迪斯可文化;不過,這些場所對當時許多年輕人來說仍是高消費,並不是大眾化的青年娛樂。
毛珊有個妹妹名叫毛適,當時她是個舞者,時常幫她姐姐的忙,後來也成為一名DJ。毛珊當時共收了二個學生,一位是她妹妹毛適,另一位便是小湯,也就是藝人湯蘭花之弟,也是我的師父,他們二人就是台灣DJ的第二代。後來因Tiffany與新加坡經紀公司合作關係的連帶影響,他們不斷地外派DJ到台灣,來來飯店也收聘從新加坡公司前來台灣的DJ;於是毛適與小湯就轉移至中央飯店,華國飯店的狄斯可舞廳開幕後,小湯便轉移陣地,各有千秋地發展自身的DJ新天地。
1980年,華國飯店的狄斯可股東們因與飯店合約談不攏,他們決定向外獨立開闢新路,於是台灣具革命性的地下舞廳黛安娜就這麼產生了。
夜總會迪斯可時期的代表歌曲
七零年代末期,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就是Michael Jackson(麥可傑克森)的<Don't Stop 'Til You Get Enough>。麥可早期從童星開始歌手生涯,在Motown(摩城)唱片時期以Jackson 5合唱團成員走紅,之後他以個人之姿發行的第一張專輯《Off The Wall》裡就收錄了這首歌,不但一鳴驚人,也帶起了全身關節都扭動不停的機械舞風潮。當時的年代流行的大家一起跳「排舞」,一群人跳著一樣的動作,然後有個領舞的舞者在前方帶動舞步,有點像是所有人一起跳體操的景象。
八零年代前的「pub」娛樂與結合音樂的餐飲場所
前述提到的第二種音樂娛樂場所類型「pub」,我們當時對它的定義是空間裡頭有吧台,有提供食物,通常也會有撞球檯和點歌機。台灣的第一家pub源自於美軍顧問團俱樂部的一位美國大兵在天母所經營的pub-FRA(Foreign Registered Association),當時僅開放持外國護照的人入場,台灣人若想進FRA消費,得有外國人偕同才能入內。消費方式也與其他地方不一樣,若想喝酒、吃東西或使用任何娛樂設施不是用現金直接購取,必須先從櫃台購買點劵,點數分五元、十元、二十元,點劵一本則有二百元、五百元和一千元為本數單位;在FRA喝酒也特別便宜,通常是其他賣酒場所的半價,因為美軍自己進口入台灣的酒水不需給付關稅。FRA的空間共有五層樓,地下室是跳舞空間,一樓是餐廳和酒吧;二樓是打撞球和玩吃角子老虎的娛樂空間;三樓是電影院,時常放一些當時台灣市面上看不到的電影或難以取得的音樂影片;四樓是他們自己的辦公室,並不對外開放。地下室當時是每週五、週六開放,每晚會有一位DJ負責放歌,通常也不玩接歌,純粹隨性地放歌讓人跳舞,於是FRA整棟充滿美式文化的生活娛樂很快地一傳十、十傳百,沒多久後,中山北路、雙城街一帶也一家接一家地開起了pub,提供吃喝之外,也有DJ在裡頭放送音樂,只不過這些仿效FRA的pub是對外完全開放,不用帶護照也可以入內消費。
第三種類型就是西餐廳和咖啡廳。這些餐飲類場所提供食物和飲料之外,大多具備自己的音樂倉庫,放滿了唱片,營業時間內都會不停地放送音樂;通常這些地方為了營造氣氛,燈光會特別昏暗,或是桌上放個燭台,顯然是適合情侶約會的場所,而當時則以新潮和青蘋果二家最具代表性,也是當時台北年輕人為之風靡的夜生活場所。
地下舞廳黛安娜的光煇時代
黛安娜的格局雖與飯店附屬的夜總會迪斯可相同,但它的營業方式卻大大不同,時間分為五個場次,分別是早場、午場、香檳場、晚場和宵夜場。早場從早上十點到下午一點,門票是一百元,一百元換一杯紅茶或可樂,大多是揹書包的學生去光顧;;午場從下午一點至五點,門票一百五十元,可兌換一杯飲料;香檳場從下午從六點到九點,門票二百元,同樣可兌換一杯飲料;晚場從九點到午夜零時,門票三百元,提供一杯飲料或一瓶啤酒,再加一籃炸雞;宵夜場則是午夜零時至清晨五點,門票三百五十元,兌換酒水和食物與晚場相同。或許在場的大家聽了會覺得有好笑,一天五個場次?不過當時的光景確實就是一種全民瘋狄斯可的盛況。那時的狄斯可不像現在夜店的門口都有保全驗查年齡,記得好幾年前遇到一個曾經在當時去黛安娜、看起來不過二十五歲的年輕人,於是問他:「你當年去黛安娜時是幾歲?」他說:「國一呀。」八零年代的狄斯可,只要你/妳敢,就可以進去跳舞聽歌。
黛安娜位於林森北路和錦州街路口,那時只要午場一結束,所有人開始散場,想續場的人再多付五十或一百元就可以留下來繼續跳舞,不過五、六百人同時離開,造成路口交通癱瘓,實在是很壯觀的景象。 那時每一場只有一位DJ,不但要放歌、找唱片、調音響,還得身兼打燈的工作,雖然不辛苦,但真的很忙。而且,還得隨時注意警報器的動靜,當警示燈一亮時,就代表「條子來了」,DJ與售票員要先”落路”,不然被警察逮捕就得關三天。當時警察若來地下舞廳抓人,會以「違警罰法」逮捕DJ或售票員,我也有過在放歌時,突然一付手銬拷住我的手,警察問:「你放唱片的?走吧」就這樣被抓去關了三天,事後老闆也包了大紅包給我,之後在DJ臺放眼望去的各個角落都加裝了警示燈,為警察來襲作好萬全準備。
回想那時當DJ真的很開心,不但能獲得自己喜歡的西洋音樂最新資訊,DJ在舞廳裡也能獨當一面,老闆也給予很大的自由,讓DJ專注在舞廳的音樂事務,至於舞客多寡和公關都與DJ無關。甚至可以這麼說,以前台灣的DJ就像明星一般,受人敬重。
將夜生活改朝換代的黛安娜
地下舞廳黛安娜不僅是八零年代具革命性的舞廳新格局,它也為當時業主和投資的股東創下極為豐厚的盈餘利潤,開業成本約四百萬元,不過從1981年至1987年的營收就高達二十億之多。正因它可觀的營業收入,1982年,規模與黛安娜相當的地下舞廳如雨後春筍般冒出,像是比利珍、瑪丹娜、名人、水牛城等舞廳,每一家生意都好的不得了,除了水牛城外,每家舞廳的營業時間都從早上開始至隔天早上,幾乎全天開放,場場爆滿,回想起來,舞廳當時真的是一門生錢行業啊。不過,那時候便產生了DJ供給不足的問題,於是各個店家開始引進香港的DJ,接著,舞廳音樂也開始出現了分歧。香港DJ的音樂滋養大多是來自歐洲以英國為主的舞曲音樂,台灣則偏向以美國的音樂居多,因此舞廳也導出了市場上的需求區隔;不過大家(DJ們)基本上都還是美國《告示牌》雜誌為參考原則。說到這本雜誌,它不只有前一百名(Top 100)的歌曲排行榜,其實書裡頭分得很詳細,有個別的舞廳排行榜、電台排行榜等音樂的細項排行榜,而當時台灣的DJ大多是追著美國前一百名的排行榜跑。
那時在黛安娜當DJ其實很幸運,由於我們的老闆經常出國,每次出國就是帶一堆新舞曲唱片回台灣,我們也因此搶得先機在黛安娜放送幾乎與世界同步的最新流行音樂。當時有趣的現象是,每個舞廳放的歌曲都大同小異,有的甚至連放歌順序都一模一樣,所以市場上的需求也產生一致性。那個年代令DJ們最為頭痛的,應該就是客人的點歌了。有些舞客不知道歌名,走向DJ台說:「欸,DJ呀,我想聽那首『喔喔喔』的。」當下常常讓DJ一頭霧水;或是因為平常聽的是台灣翻版唱片,上頭印製的英文歌已譯成中文,舞客們就用中文歌名向DJ點歌,例如遇到的客人曾點:「DJ,我要聽<自制力>。」當下也是讓DJ想破頭這歌名的原文,過好一會兒才恍然大悟,原來是Laura Branigan的<Self Control>。
從DJ師徒制漸漸獨立出自身名號
八零年代後,台北的地下舞廳琳瑯滿目,DJ也跟著變多了。一開始跟著DJ小湯當他的學徒時,起初的日子都是幫師父提唱片箱、整理唱盤、DJ臺和唱片櫃,之後慢慢地開始可以接手師父休息的時間放歌,但無法掌控全場;我一直到1982年左右才開始以個人DJ身份獨立自主。那時DJ的平均月薪是二萬八千元,一天放歌三小時,外加公司百分之十的紅利,一天可以吃一籃炸雞,喝無限量供應的可樂。以八零年代的台灣幣值來看當時的DJ月薪,等同於一個銀行經理的月薪,可以說那時當DJ是賺錢的好頭路。由於DJ的需求增加,除了引起香港DJ,1985年也陸續引入其他國家的外籍DJ,像是菲律賓、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DJ。聘請菲律賓的DJ來台灣放歌,費用比其他國家的DJ要來的便宜,星馬地區的DJ相較於台灣的DJ,其肢體語言相對豐富且充滿活力,在台上帶動跳的本領更是一流。於是台灣舞廳也跟著衍生各種風格的DJ,無所謂好壞,舞客們各有各的喜好,同時也因各國聆聽的音樂文化不同,各國DJ所放送的音樂也讓台灣舞廳音樂更多樣化了。
當時星馬地區的DJ偏好曲風大多是以放克樂(funk)為主,台灣DJ以美國流行音樂排行榜或英國的舞曲音樂為主,香港DJ則是傾向歐洲流行的舞曲音樂;不過,一切地下舞廳無論是DJ風格或音樂風向都在1985年另一間當時全台灣最大型的迪斯可KISS Disco的開幕而產生遽變。
KISS Disco締造的迪斯可光景
這間位於敦化北路中泰賓館的迪斯可一開張後,全台北的地下舞廳幾乎全部掛點,KISS讓這些舞廳無法繼續經營的主要原因,是因為它大的足以一次容納二千人,一張門票三百五十元,每晚僅一場,加上最炫的燈光和音響設備,讓當時所有台北舞客都趨之若騖,而KISS也一直到2003年才正式結束營業,期間經過四次整修,然而能在台灣舞廳和夜生活佔有二十七年的歷史,已是相當驚人紀錄。
KISS開幕之後,林森北路一帶的舞廳逐漸沒落,大家開始轉移陣地至台北東區,
那時余天的弟弟余龍(已逝)在東區開了一間名為99的迪斯可較具知名度,也吸引了不少原本流連KISS的舞客前往朝聖;爾後高凌風接著在長安東路開設一間位於頂樓,每到午夜零時,天花板就會打開變天窗的夢幻迪斯可舞廳「閣樓」(Penthouse),它的特色就是不但請來新加坡能DJing又善舞的俊俏DJ,也有樂隊與合唱團作全套的音樂演出,整體氣勢加上聲光效果吸引了不少舞客,也因此促使了第二間位於西門町的「西閣樓」迪斯可的誕生,但是營業績效並不如預期的理想。
在二家閣樓舞廳之後,也開設二家別具特色的迪斯可舞廳,一間是在以前環亞百貨的NASA,另一間則是位於八德路上的SOHO Disco,格局不亞於KISS,但這些舞廳始終無法突破KISS的紀錄榮光。八零年代的舞廳起起落落,晚期近九零年代時,歌手齊秦與其他影歌星,以及時尚名流在民生東路上開設一家名為「I LIKE」的迪斯可舞廳,那時舞廳文化也即將步入終結。
八零年代舞廳裡的流行音樂
當時舞廳流行的曲風多為新浪潮(new wave)、龐克和前衛電子音樂(這裡Stephen前輩所指的應是Synthpop曲風),像是當時讓藝人張小燕在《綜藝一百》節目上跳舞選用的歌曲<Wordy Rappinghood>,這首來自Tom Tom Club樂團的歌曲便是在舞廳裡的新浪潮曲風代表;另外英國Yazoo樂團的<Don’t Go>也是當時火紅的舞曲。到了1982年,Michael Jackson風潮又回歸舞廳,他的專輯《Thriller》打破太多音樂紀錄,在全世界掀起的潮流無人能敵之外,也象徵了音樂試圖破除種族主義根深蒂固的隔閡。專輯裡邀來與披頭四成員合唱的<The Girl Is Mine>,以及與吉他之神Eddie Van Halen合唱的<Beat It>,這二首都是八零年代早期的超級經典。接著1985年,又出現一首轟動台灣地下舞廳的歌曲<Shout>,也就是英國樂團Tears For Fears(驚懼之淚)的經典名曲,當年這首歌在台灣出現時,著實考倒了不少DJ;要將這類BPM 90左右的慢板歌曲與BPM 130、140的舞曲流暢地銜接在一起並不容易,那時給了DJ們不小的衝擊與考驗。不過也因為DJ們開始尋求將這些快板和慢板能流暢銜接的中速歌曲素材,台灣舞廳的音樂風格也因而變得更多樣化,DJ們不再只侷限於追求告示牌美國排行榜上的歌曲。隨著台灣的英文雜誌社進口《告示牌》雜誌,DJ們也開始深度挖掘和聆聽如舞廳、電台、再混音(remix)等各種類型的歌曲排行榜,我自己也因為當時在ICRT工作的關係,電台同仁也指導我應該細究所有類型的歌曲排行榜,甚至還有成人分類的排行榜,也就是十八歲以上才能聆聽的歌曲。
八零年代中期,英國的流行舞曲在台灣又起浪潮後,也連帶激起歐陸舞曲的波浪,當時紅遍舞廳的代表歌曲就是由義大利團體Baltimora所做的<Tarzan Boy>(泰山男孩),那時騎名流150、車上若裝音響的年輕人沒放這首歌就遜掉了。1987年之後,在台灣舞廳放歌的DJ們也開始放送黑人的節奏藍調和搖擺樂風的歌曲,八零年代晚期的代表像是Karyn White(Baby Face為她製作的同名專輯)、Aretha Franklin,以及鼓手Narada Michael Walden自己譜曲製作專輯的歌曲都是當時DJ們會在舞廳放送的音樂。然而,縱使舞廳音樂的曲風越來越豐富多變化,DJ也想嘗試放送新的歌曲,當時卻也讓許多舞客無所適從,有些舞客仍堅持在舞廳聽自己想聽的歌曲,因此點歌文化在舞廳仍是不退之流。